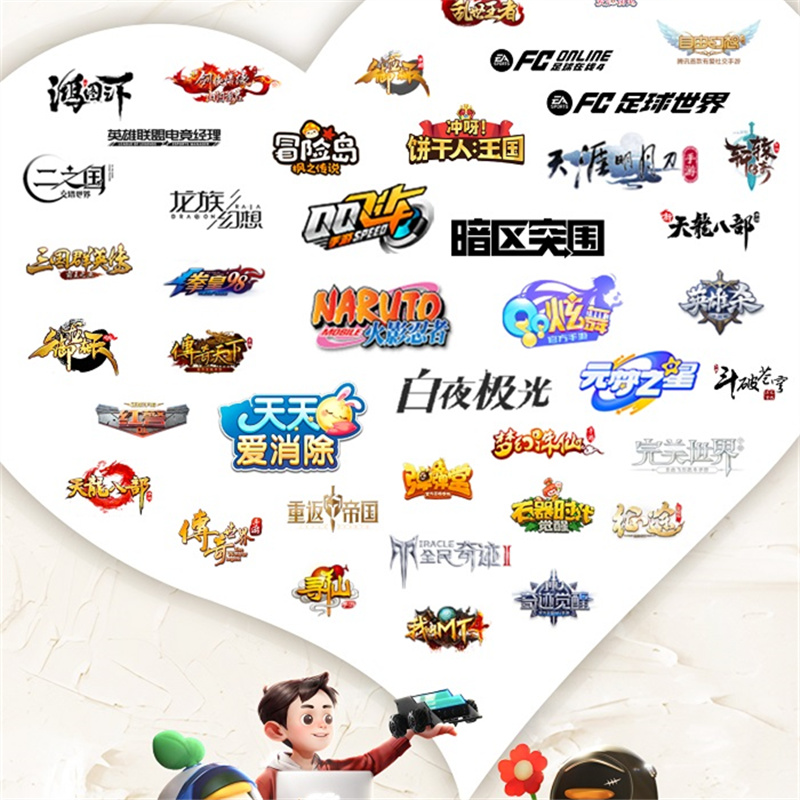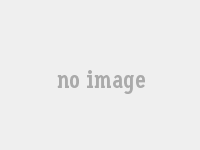网络互助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自带光环的争议性存在。“相互保”事件,更将网络互助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从社会保障价值,特别是重大疾病保障的视角来看,网络互助有效弥补了底层社会医保与上层健康保险中间的“保障真空”,为社会中低收入的“夹心层”提供了一种普惠式的有效保障补充,毫无疑问是一个有益的创新探索。从某网络互助平台已发生的数百件互助事件看,30-40岁之间的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支柱人员占比为63%,相对生存压力比较大的中低收入职业人群累计占比高达80%,网络互助对于社会中低收入患病人群的帮扶作用明显,体现出较为突出的社会价值。然而,关于网络互助的未来,从当前看,尚没有一条明确的出路。
网络互助的“生存三角”
困扰网络互助生存发展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在于“我是谁”的终极之问。保险?公益?还是互联网信息撮合平台?身份的明确定位在哪,最终决定网络互助的未来之路到底指向何方。
对于网络互助是否属于保险,保险监管的态度是一贯明确的,先后两次进行风险提示,更是在2016年12月的专项整治工作中,提出5条具体整改要求,明确划定网络互助与保险之间的清晰界限,敦促网络互助规范运营,加强整顿,不得跨越红线。严格按照保险的契约要件以及当前的法律体系看,网络互助不是保险几无争议,网络互助的“保险之路”不通。同时,保险监管机构的举措,关键在于厘清网络互助与保险之间的界限,维护广大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并未对这一创新模式进行“一刀切式”的否定,体现出对于网络互助价值的肯定和对创新的包容。
投奔保险无望之后,不少网络互助陆续申请公益牌照,转型公益,并高调对外宣传自己的公益身份。然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捐赠是一种“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是一种单向的、不针对特定对象的赠与行为,不能预期获得风险保障回报,更无对双方的有偿协议约束。而网络互助针对特定参与会员,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契约精神,其本质上是双向的、受强制契约约束的、有条件的赠与行为,会员的“赠与”主观上在于“自利”而非单向“利他”,与真正的慈善有本质不同。2017年7月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明确指出:“个人求助、网络互助不属于慈善募捐……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杂”。从业务实质,到法律依据,乃至监管主体上看,网络互助的公益身份并未得到相应认可。
除开保险与公益之外,互联网平台成为网络互助唯一名正言顺的身份。如此以来,作为科技型企业,网络互助平台只需在工商局进行注册,发布的网络互助计划作为科技产品,则理应由工业与信息部门进行监管,并不需要其他专门的业务经营许可证。然而,网络互助实质构建起一种互助性的经济组织,提供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科技产品,且涉及货币往来,仅仅由工业与信息部门进行属主监管,似乎并不符合网络互助的经营本质,并不能对其核心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况且,网络互助平台本身,以及推波助澜的资本,并不满足于互联网平台这一定位。没有其他身份的标榜和加持,网络互助也就失去了其在供给侧的吸引力。
“公益”的网络互助为何会得到资本青睐?
网络互助自模式诞生以来,便受到资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16年,成为各路资本竞相入主网络互助的争夺年。尽管经历了2017年网络互助领域的洗牌,数十家网络互助平台陆续倒闭,存活下来的很多平台纷纷转型公益。然而,整个过程,资本对于网络互助的热逐并未停止。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数十家网络互助平台对外融资合计约8亿元,壁虎互助更是于2018年6月获得1亿元B轮融资,资本对这一领域热度不减。由于慈善公益具有不可盈利和出资不能转让的特性,真正的慈善公益并不是资本热衷的领域。那么高调宣扬公益身份的网络互助平台,为何能够得到逐利性资本的青睐呢?
各路资本之所以在网络互助领域积极投入、争相布局,总结起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觊觎保险牌照,“曲线救国”分享保险蛋糕。在我国,保险属于许可经营领域,传统保险牌照在注册资金、股东资质等方面门槛较高,绝大多数资本很难进入,保险牌照是一种稀缺资源,于是一些资本希望通过网络互助形式,在保险领域分食一杯羹。二是看好网络互助平台的流量聚合效应,积极寻求流量变现。以抱团取暖和归属感为主要特征的网络互助,完美契合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惧感与孤独感,提供了满足特定群体健康“刚需”的互联网产品,且门槛低,性价比高,有人文关怀,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具有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众多网络互助平台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已坐拥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注册会员,成为聚合客群的重要流量平台,非传统线下渠道可以匹敌。一些网络互助平台借助用户流量,各显流量变现神通,甚至代销瓜果蔬菜和生活用品,互联网经营思维尽显其极。三是看重网络互助平台生态,积极布局大健康领域。网络互助提供的是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健康产品,具有相关健康需求的用户,在健康领域具有普遍较高的用户粘性和忠诚度。基于网络互助平台,进行健康交易场景嵌入与健康产业上下游延伸,可以有效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健康管理生态,进而布局大健康领域,分享巨大的健康产业红利。
毋庸置疑,网络互助能够发展至今,资本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没。而且,网络互助未来要想在社会上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挥其积极作用,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然而,在市场环境下,资本始终是逐利的。如何恰当地规范和引导资本服务和支持网络互助发展,同时又不挫伤资本的积极性,是网络互助发展过程中需要权衡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公益并非网络互助最好和最终的归宿
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相关整改措施,网络互助平台不可以设立资金池,也就断了平台借助资金池生利的路径。同时,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下,不少网络互助平台承诺不收取管理费用,甚至在资本推动下降低入会门槛,大打补贴战,抢夺用户,加之平台本身的运营和管理费用高企,使得平台获客成本畸高,一些网络互助平台的获客成本甚至高达400元。网络互助平台支多收少,缺乏明晰的商业模式,短期内看不到实现盈利的希望,平台运营和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谓的“低门槛、高保障、高性价比”是网络互助最初兴起的根本诱因,同时也成为困扰网络互助持续生存下去的可悖之处。在合规和生存压力下,为保住用户流量,谋求生存空间,不少网络互助平台纷纷转型公益,逐步走向“左手公益,右手商业”的运营模式。
实际上,无论从法理方面看,还是从运营实践中看,“左手公益,右手商业”的模式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尬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相关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是慈善公益组织的核心特征和首要前提。被众多投资机构加持的网络互助平台,在逐利性资本的驱使和胁迫下,也许并不尽然一心踏实做公益,而是将网络互助平台作为一个“流量平台”,并借此打造交易场景和商业模式继而“薅用户羊毛”。由此,网络互助平台或许“以公益慈善之名,集聚流量用户,而行商业营利之实”,转型公益后的网络互助平台“左手公益,右手商业”,一手托两家,并不一定能够全然做到“公私分明”,最终“在一个口袋里算账”在所难免,孰轻孰重自然是“账房先生”掂量着办。这种模式看起来解决了网络互助平台的生存出路问题,但是消费者的权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还可能会对社会民众的慈善之心造成伤害,使得民众对于社会公益慈善产生质疑。况且,网络互助平台的公益身份本就存疑,并非名正言顺。如此来看,网络互助转型公益,似乎只是网络互助创新探索过程中的权宜之策,更像网络互助“曲折式前进”过程中折回的那一步。网络互助的未来发展终局定不在此,公益并非网络互助的最好的归宿,也必将不会是其最终的归宿。
社会民众权益最大
考量一个行业或领域是否有真正价值的核心标准,在于其本身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就是这一行业或领域对于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空间。从这一衡量标准看,网络互助无疑是具有价值的,不但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有效满足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众的健康需求,而且对社会整体保障体系形成有效补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和管理负担,能够极大提高社会民众在健康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符合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的创新路径。创新的过程总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有挫折,走弯路,甚至有可能出现反复。在创新探索前进的过程中,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至关重要,要肩负起鼓励、引导和规范的重任,其最终诉求和基本出发点在于,要将切实保障实现社会民众权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积极谋求整体社会福祉不断提升。在网络互助的创新方面,要想实现这一领域参与社会民众的权益最大化,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网络互助平台的可持续性。网络互助对于社会福祉的改善效果是明显的。要想真正实现社会民众权益最大化,就要确保网络互助机制有效运行且具有经营可持续性。影响网络互助平台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相对明晰的监管路径下实现合规化的创新进步;通过切实满足用户健康需求和权益的互助计划推动用户规模实现不断增长;探索可以实现自我造血和持续经营的平台运营商业模式。其中,既包括监管和市场维度的外部因素,也受到平台自身经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网络互助平台不断提高产品满足社会健康需求的契合度和性价比,同时不断提升平台自身的稳定、安全、持续运营能力,是推动行业内外部环境向利于网络互助发展方向演化的根本和基础,也是实现社会民众权益最大化的核心和保障。
二是保险行业与公益领域的声誉。按照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体系,从严格意义上看,网络互助既不属于保险,也不属于公益。但是,在网络互助实践中,供需两端有意或无意地,容易模糊行业边界,带来不必要的误解和伤害。对于网络互助平台而言,为了迅速累计平台注册用户,做大平台流量,不少平台选择蹭保险的“流量”,或者兜售慈善公益情怀,在对外宣传推广过程中,含糊其辞,给社会民众带来一些联想和误解。对于普通社会民众而言,由于缺乏专业认知,或许会轻信平台的宣传,自觉不自觉地将互助计划与保险保障联系起来,或者将平台作为一种通常的慈善捐赠,而因此被一些平台绑架,成为一些平台谋取私利的牺牲品。如此,最终受到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对历尽艰难和曲折累积起来的中国保险行业与慈善公益领域声誉的伤害。一旦社会民众因此受伤,积怨和不满将在网络上快速传播,或许会形成不利于保险和公益的舆论导向,这是对整体社会利益最大的伤害。
三是明确有效的行政监管主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网络互助计划产品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同时在受益上非排他,溢出效应巨大,具有明显的社会正外部性,属于一种较为典型的准公共产品,此时市场机制失灵,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为保障社会利益最大化,建议对网络互助实施有效监管,明确行政监管主体。另一方面,网络互助业务的核心,实质上是对资金的撮合和对资金流管理,是较为典型的货币流通行为,具备明显的金融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目前的网络互助除了未承诺还本付息外,其他行为特征与非法集资行为特征高度相似,平台资金运营金融特征明显,具有很高的金融风险。在没有明确监管主体的引导和规范的情况下,如果网络互助发展不及预期,资本在一阵狂欢后黯然离去,留下一地鸡毛,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广大社会民众。鉴于网络互助的相关特点和属性,为充分保障社会民众的权益最大化,同时保护和推动网络互助创新向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建议将网络互助逐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最终由银保监会进行属主监管,加强有效引导与规范,促使网络互助创新的普惠红利惠及更多社会民众,推动社会整体福祉的改善和提升。